張愛玲小說中的這幾句話大家都耳熟能詳:“也許每一個(gè)男子全都有過這樣的兩個(gè)女人���,至少兩個(gè)���。娶了紅玫瑰,久而久之�,紅的變了墻上的一抹蚊子血,白的還是‘床前明月光’�;娶了白玫瑰,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飯黏子�,紅的卻是心口上一顆朱砂痣”。張愛玲的這篇《紅玫瑰與白玫瑰》寫于一九四四年�����,小說中的佟振保既不敢接受王嬌蕊的熱烈(紅)�����,也難愛孟煙鸝的“霧數(shù)”(白),一個(gè)想做“對(duì)”的人卻怎么做都“不對(duì)”─“不對(duì)到恐怖的程度”�。
佟振保的困境顯然不只屬于他一個(gè)人。早在一九二八年�����,茅盾就在他的小說《詩與散文》中���,塑造了一個(gè)佟振保的前身“青年丙”的形象�。這個(gè)“丙”心中有一個(gè)“抓得住我的心靈的女子”─他的表妹���。聰穎的表妹“似乎早已窺見他的隱衷”�,在送他鮮花的時(shí)候這樣對(duì)他說:“丙哥�,你喜歡這些白玫瑰么?希望你只看見潔白芬芳的花朵���,莫想起花柄上的尖利的刺罷����!人生的路上,有潔白芬芳的花���,也有尖利的刺,但是自愛愛人的人兒會(huì)忘記了有刺���,只想著有花�����!”
果不其然�����,當(dāng)“青年丙”忘情于對(duì)表妹的心靈沉醉時(shí)���,現(xiàn)實(shí)生活中還另有一個(gè)女性纏繞著他─那是“一天一天的肉感化,一天一天的現(xiàn)實(shí)化�����,一天一天的粗淺化”的有著“玫瑰一般可愛的嘴唇”的桂�����。在“青年丙”的心目中���,“男女間的關(guān)系應(yīng)該是‘詩樣’的─‘詩意’的”�����,“詩樣的感情”才是“女性的特有品”���,而他現(xiàn)在面對(duì)的桂�,卻“太快地進(jìn)了平凡丑惡的散文時(shí)代了”�。
如同振保在紅玫瑰(王嬌蕊)和白玫瑰(孟煙鸝)之間舉措“不對(duì)”最后“紅”“白”皆失一樣,“青年丙”也在“詩”(表妹)與“散文”(桂)的選擇中“竹籃打水一場(chǎng)空”�,“詩”與“散文”最終都離他而去─“只想著有花”而“忘記了有刺”的人生,顯然不是“對(duì)”的人生�����。
紅玫瑰與白玫瑰也好�����,詩與散文也罷���,說到底都逃不出錢鐘書筆下的那個(gè)“圍城”���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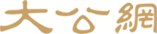

 京公網(wǎng)安備11010502037337號(hào)
京公網(wǎng)安備11010502037337號(hào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