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圖: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大公報(bào)刊載《天津的小飯館》。\作者供圖
從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七年���,立足天津的新記大公報(bào),在吳胡張三駕馬車的率領(lǐng)下��,漸成影響遠(yuǎn)達(dá)全國的報(bào)業(yè)巨擘���?!坝腥菽舜?����,包羅萬象”的大公報(bào)�����,不僅涵蓋政治軍事、經(jīng)濟(jì)商業(yè)����、藝術(shù)科學(xué)的重要新聞、評(píng)論�����、知識(shí)����,即便衣食住行等報(bào)道,亦有聲有色�����,“天津衛(wèi)�����,三宗寶����,鼓樓炮臺(tái)鈴鐺閣,永利南開大公報(bào)�����,銀魚紫蟹大紅襖?!碧旖蛉说娜粘?���,離不開大公報(bào),也離不開“銀魚紫蟹”等吃食���。
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起���,大公報(bào)連續(xù)九日,在《本市附刊》頭條連載了一組《天津的小飯館》�����,堪稱一部簡潔版的天津美味指南����,名副其實(shí)的“津津有味”。作者的寫作緣由是華界繁榮沒落后�,大飯館紛紛遷入租界,有感滄桑巨變�����,便將目光聚焦到“普遍在中小社會(huì)里的小飯館”。立意非常明確:“倘為擺動(dòng)闊綽��,自當(dāng)走向大飯館里──那里只能給你一種奢侈印象��,錢多費(fèi)了但仍不敢保你吃得飽���;若為吃飯而吃飯���,則須往一般平凡的飯館走去?���!?/p>
因此,作者精細(xì)素描了路邊攤�����、宵夜�����、二葷舖、小酒館����、清真館、包子舖�����、素菜館�����,有知名的老字號(hào)�����,也有攤販叫賣的包子����、煎餅��、玉米餑餑……這從各篇的小標(biāo)題就可直觀感受出來:《宵夜飯館各式皆備》《勞動(dòng)階級(jí)席地而食甘之如飴》《餃子大餅別具一格》《羊肉包舖生意獨(dú)盛》《冬令既屆涮羊肉大利市》《秫米飯舖點(diǎn)心齊備》等�����,無不透著濃濃的煙火氣和市井味道�。
比如“小熱酒舖”���,“門外只懸著一個(gè)酒壺的模型當(dāng)做招牌,里面只有一些簡單的酒菜�����,如鹹花生���、辣白菜等”“負(fù)苦的人只有三十個(gè)銅子的大餅����,兩個(gè)銅元的咸菜���,便已解決了問題”“更經(jīng)濟(jì)些的���,拉洋車的,隨便有幾個(gè)玉米麵餑餑──只要兩個(gè)大銅元一個(gè)──也一樣抵得一日之糧�。”
“豬羊肉包子舖”���,則高檔一些�,各餡鍋點(diǎn),里面有蝦仁��、蟹肉��、海參�����、雞子等��,普通餡則只有肉�,眾口同養(yǎng)。而“餃子舖”──“餃子俗稱‘老虎爪’���,餃子舖為供給迅速、伺應(yīng)敏捷起見���,多在午飯前�,很早把餃子煎出多許�,放在一旁,到‘飯口’忙時(shí)���,只重新放在鍋里加上香油�,便可賣錢?����!?/p>
至于天津的地方特色小吃──煎餅���,文章則寫道:“在法租界勸業(yè)場�、馬家口���、日租界四面鐘�����、新旅社前����,更有一種專門賣‘煎餅果子’的����,也一直賣到夜深三四點(diǎn)鐘,雖是一種宵夜點(diǎn)心�,亦可視做夜飯的”。根據(jù)天津地方學(xué)者的考證��,這是“煎餅果子”一詞,首次出現(xiàn)在報(bào)紙這一大眾傳媒上���。前些年���,圍繞煎餅究竟是“果子”還是“馃子”曾引發(fā)了兩派之爭,而大公報(bào)的寫法��,起到了一錘定音的作用����。
《天津的小飯館》組稿,還記錄了當(dāng)時(shí)天津飲食的諸多新現(xiàn)象���。比如《素菜葷做的有藝術(shù)頭腦》����,“把素的豆腐面筋豆皮等��,特制成雞魚鴨肉等葷菜模樣�,甚具匠心�����,頗有藝術(shù)頭腦?!庇秩纾恍┲饕獮檠笮腥A人雇員或青年學(xué)生提供便餐的飯館�����,為了招徠顧客�,爭相利用新式的女招待做噱頭──“因此,‘本館新添女子招待’的招牌���,便與‘本館新添什錦火鍋’的招牌一樣擺列門首�����?�!?/p>
不同地方特色的飯館�����,在天津也有不同的際遇變遷:“山西館在晉系(閻錫山)執(zhí)政時(shí)���,很曾興盛一回,這里的食品��,有許多是不與一般飯館相同的,如‘刀削’‘撥魚’……只是為趨時(shí)尚�����,便很有些山西館數(shù)典忘祖的���,只管拿他們不能擅長的食品饗客�����。至于所謂的南式飯館��,則因口味的不同��,顧客以江南客籍人維多�,誘因價(jià)錢昂貴��,津人亦唯有中小資產(chǎn)階級(jí)偶一嘗試而已�。”
由于作者是地道天津人���,對(duì)于各式美食分布,瞭如指掌���,娓娓道來:“南市一帶�,在燕樂升平對(duì)過,有二葷館久華春�、山東館聚合樓和岳陽樓三家,以外盛德里��,侯家后�,西關(guān)外,西南成交�����,河北大街……各式小飯館�����,包子舖���,餃子舖�,賣豆沙各餡包子附帶‘嫩肉’的小館����,賣五香醬牛肉的飯舖……”儼然如一副民國天津版的“清明上河圖”。對(duì)于研究近代天津社會(huì)�、商業(yè)����、餐飲業(yè)�����,是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�����。
這也是大公報(bào)“筆錄歷史”的另一種特殊作用���。在這張大報(bào)的雙甲子歷程中�����,不僅僅有歷史風(fēng)云的宏大敘事�,更藏著升斗小民飲食起居的種種細(xì)節(jié)�。
我們還有必要記住這位作者。這組活色生香的報(bào)道����,署名“墨農(nóng)”,即當(dāng)時(shí)大公報(bào)采訪部負(fù)責(zé)本市新聞的記者林墨農(nóng)。從文字筆觸來看��,這位參透飲食經(jīng)����、大得生活趣味的報(bào)人���,似乎是個(gè)優(yōu)哉游哉的小市民�。其實(shí)�,他又是一位英勇無畏、頂天立地的好漢����。
一九三七年八月,天津淪陷����,大公報(bào)主力人馬播遷上海。大公報(bào)采訪部主任并兼本埠新聞編輯顧建平���,以及兩位老部下林墨農(nóng)���、孔效儒,加上原天津《益世報(bào)》記者程寒華,冒著生命危險(xiǎn)�,克服重重困難,用鐵絲�����、網(wǎng)布����、廢舊膠輥?zhàn)灾屏艘患苤`寫油印機(jī),并天天到一位友人處“借聽”廣播收音機(jī)來收集消息�,出版了秘密小報(bào)《高仲明紀(jì)事報(bào)》,宣傳抗日�。
四人分工新聞、特寫報(bào)道���、社論�����、短評(píng)��、印刷�����、秘密派報(bào)����,大受愛國市民歡迎。從創(chuàng)刊首日只印三十份���,兩個(gè)月后印量就達(dá)千份。此事后來引起日寇高度注意���,一九三九年九月終被日本憲兵隊(duì)搜查破壞�����。林墨農(nóng)等人提前獲知新消息����,安全撤離天津到了大后方��。堅(jiān)持每日秘密出版達(dá)兩年之久的《高仲明紀(jì)事報(bào)》從此畫上句號(hào)���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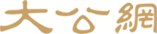


 京公網(wǎng)安備11010502037337號(hào)
京公網(wǎng)安備11010502037337號(hào)